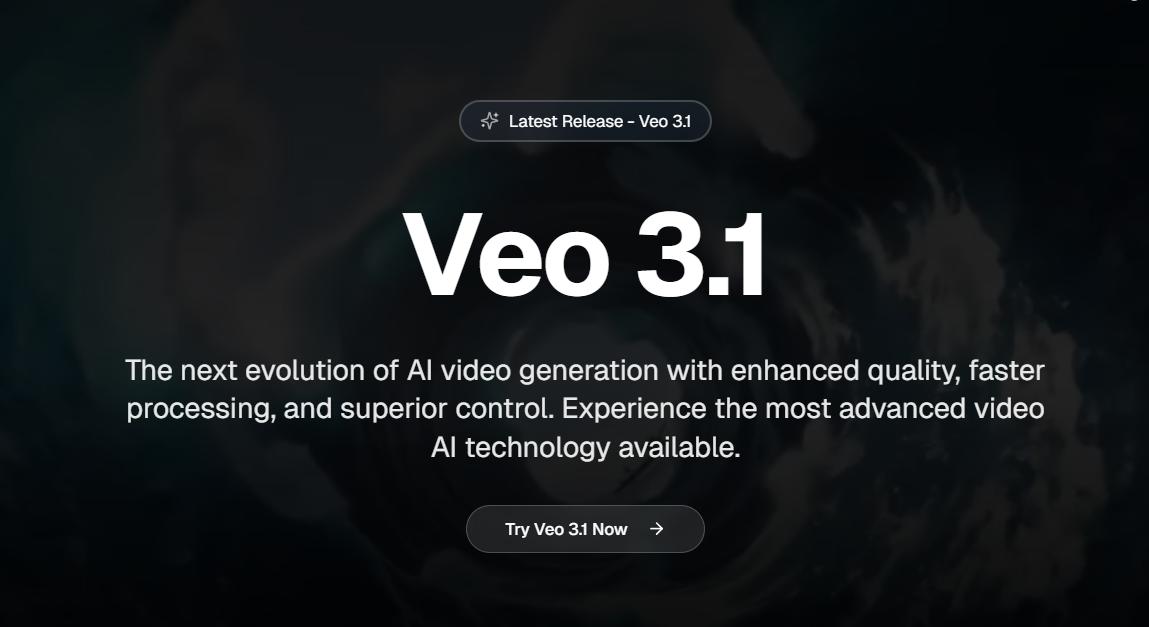麦哲观点

【麦哲观点】从英国到中国,全球船舶制造业三次变革——下一轮技术趋势是什么?
时间:2025-09-09

01 船舶制造全球变迁史
全球造船业中心经历“英国→日本→韩国→中国”三次转移后,行业已从成本竞争转向技术竞争,技术代差取代成本优势成为竞争壁垒,已开启新一轮技术革新期,在此趋势推动下,我国船舶制造正迈向由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。
第一次转移:从英国到日本——工业先发优势的丧失与成本驱动的崛起
英国首个造船中心,崛起凭借两大核心支柱,一是殖民扩张带来大幅提升的船舶制造需求,二是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先发优势,将蒸汽机技术及钢铁率先应用在船舶制造上,取代传统的木船与风力船,19世纪中叶,成全球第一造船大国,但二战为第一次转移埋下伏笔,随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贸易控制力弱化,及国内采取去工业化政策,对造船技术投入有限,技术停滞不前,叠加日本低人工成本冲击,造船业份额加速下滑,逐步失去主导地位。
日本造船业的崛起,恰好承接了此次转移机遇。起步于19世纪后叶,通过政府干预确立“海运立国”方针,为造船业打下坚实基础,二战后虽因美国制裁短暂停产,但1949年全面复工后,凭借三大核心优势——人工成本优势、精细化生产及政策扶持,造船份额快速提升,在1956年完工规模超越英国登顶,造船中心易主日本,后随成本和政策优势减弱,及高端研发不足,竞争力下滑,造船份额被韩日相继蚕食,2000年,被韩国超越,2008年被中国超越。
第二次转移:从日本到韩国——反周期布局与高端技术突破的胜利
日本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并未长久维持,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显露疲态,随成本和政策优势减弱,过度依赖中低端船型对高端研发不足,技术迭代放缓,造船份额被韩国蚕食,韩国凭借差异化策略快速崛起,推动第二次全球转移。
韩国造船业的起步依托于历史基础——二战后接管了日本殖民期间遗留的船厂,初步具备产业根基;此后通过三大关键举措实现突破:一是政策与资本的强力赋能,韩国政府通过立法明确造船业的战略地位,提供大额财政补贴、低息贷款,并推动现代、三星、大宇等财团企业入局,整合资源形成规模效应;二是精准的反周期操作,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下,在全球多数造船企业收缩产能的背景下,采取反周期操作,通过扩充产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;三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,韩国进一步聚焦高端技术攻关,打入高附加值市场,2003年韩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全面超越日本。
第三次转移:从韩国到中国——全产业链优势与全球化红利的爆发
韩国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在21世纪后遭遇中国的强力挑战,造船业市场份额下滑,第三次全球转移随之开启,2010年三大指数被中国超越,目前仍主导高端船型。
中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历经长期积累:50年代在原苏联技术援助下奠定现代造船工业基础;在1978年改革开放,2001年加入wto,事件推动下,全球贸易扩张带动船舶需求激增,凭借完整产业链、成本优势、政策支持,造船迅速崛起,2008年中国造船产量超越日本,2010年三大核心指标全面超过韩国,跃居世界首位,标志着全球造船中心第三次转移完成。目前我国处于由大到强高质量发展阶段,主导中低端船型,在高端船型也取得不断突破。

02 船舶制造发展趋势
全球船舶制造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,绿色船舶凭借政策驱动与减排需求已成行业发展主流,智能化正全方位赋能产业生态,海上风电新兴市场迅速崛起拉动特种船舶制造需求,行业发展空间再扩容。
从产业转型看,绿色船舶已成主流。据克拉克森数据,2024年全球新造船订单中,替代燃料船舶占比以修正总吨计达61.07%,首次突破半数,绿色船舶已成主流,绿色船舶中,LNG(50.32%)、甲醇(23.53%)、氨燃料动力船(13.48%)为主要方向,其中技术成熟的LNG动力船成绿色转型主力军,甲醇、氨燃料动力船舶虽供应链尚未成熟,因其零碳排放潜力,正成为未来深度脱碳关键方向。
从技术赋能看,智能化浪潮在全方位重塑船舶制造产业生态。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与船舶制造深度融合,已在船舶设计、建造、运营及维护核心环节落地应用,在数字化设计平台、数字化车间、“5G+工业互联网”、智能感知设备、自动化航运、智能导航等取得突破,受硬件成本高企、人才短缺、数字孤岛、复杂海况等制约,整体应用处于发展阶段,呈“点状突破、系统待合”的发展特征。
从应用端看,新兴市场需求崛起,行业空间再扩展。新兴市场需求异军突起,成为拉动船舶制造行业发展的新引擎。海上风电产业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,带动安装船、起重船、运维船和运维母船等特种船舶市场需求增长。